你认为人的主体性是不可侵犯的,因此你顽固而坚强的恪守在自己的世界里,遵循一套自己在可触及的现实世界中有效且可行的秩序。
尽管不时的,文化与亚文化渗透着你的世界,让你还能做些颇有价值的白日梦,但至少这还是主动的,而非简单地把自己交给时代的潮流(风尚,主流,抱歉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描写和合适)来随波逐流。
所以对你来说,互联网未免也太可怕了。对于个人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和道德观念的践踏,取笑和无视已经是最无足轻重的罪过,而尊敬和礼貌则是一种奢侈;尽管你认为这是人类之所以文明化的原因。
人类的主体性总是渴望着奴隶和客体的奴役。在非劳动化的现代话语中,这种欲望转变为了认同与被认同,慕强与控制。在相同的话题中,人们对理解不感兴趣,而是通过可以物化或量化的方式来决定个体和思想应有的地位和价值。尤其是当个人的话语权和个体本真的重要性被人数和大众认知所消解时,这将会体现的更为明显。
而为了物化与量化个体,人们则自然而然的发展出一套结社/团体/圈子/俱乐部模式,通过隐形/有形,强迫/非强迫式的规则来测试个体的服从性和对某种特定认知方式的接受程度。在这种条件下,理解的的作用责备量化的个体所产生的指标和符号替代了;在舞台理论的前提下,人也会逐渐靠近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不去和团体的秩序产生冲突。
在此中前提下,自由是否必然伴随着物质上或是精神上的孤独呢?我目前没有答案,或者说,人们对于自由的定义或许就已经过于宽泛了。
或许人渴望的并不是自由,而是所属与自己的主体性最大程度的扩张和侵略,来保正“自己做的事情都对”。我始终不明白对个体而言,当违背自己的“客体的自由”不作为模糊的概念,而是客观的的需求后,我们是否还能如此自然的高呼自由作为人的根本需求呢。还是简单把自由总结为“大多数人的自由,权力者的自由”更合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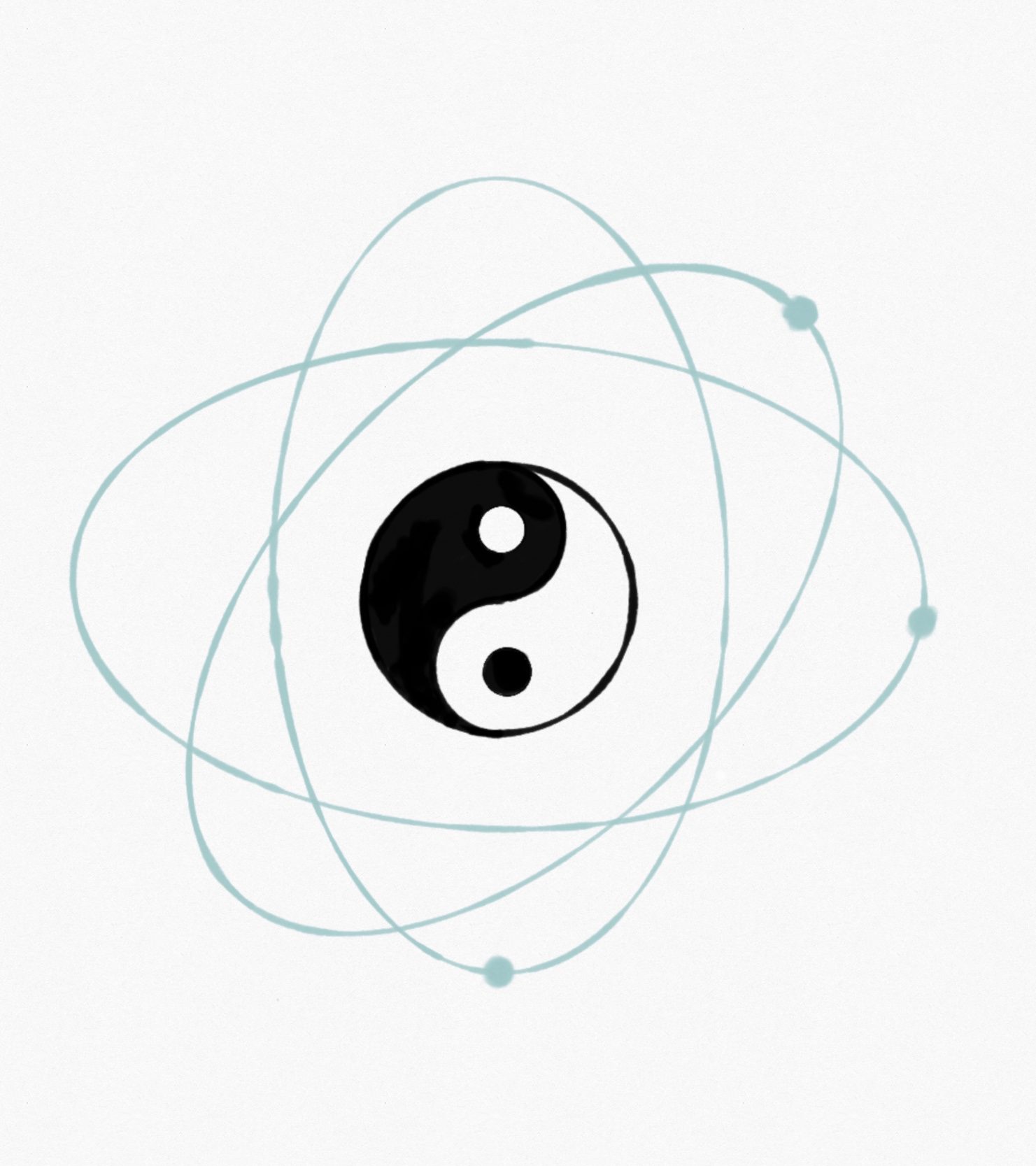

v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