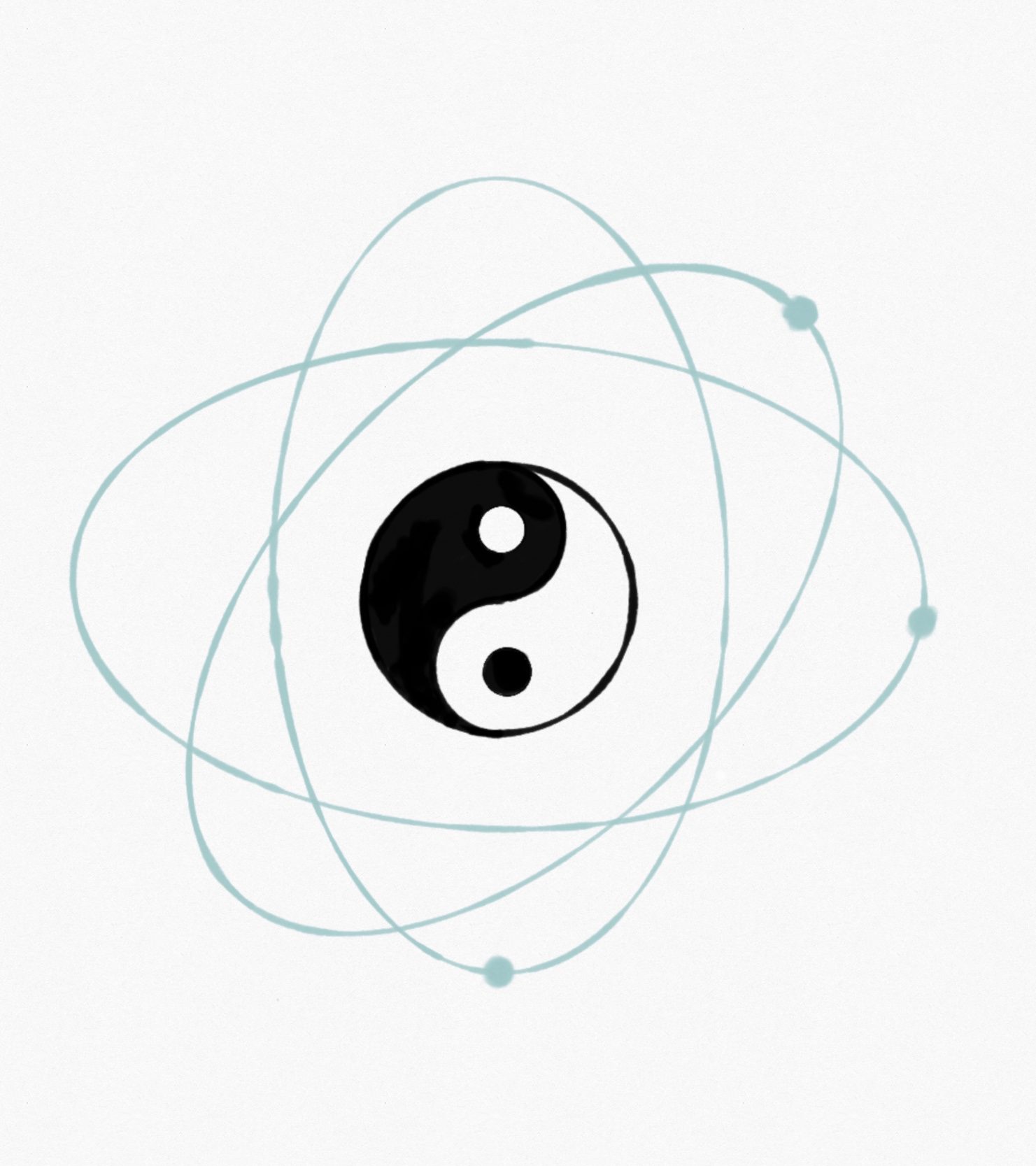业这一词大概是出自佛教,又在东亚文化不同的语境下延伸出相似却不尽然相同的意思。
传统的中文解释中,业的概念更接近于罪孽,是人类一生中所做的恶事造成影响的总和。因此也常有业果一说。而这个概念又常常能从董仲舒所申引的天人感应学说中找到一些端倪。无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或是底层的黔首,其所做所为,都以“德”的标准来衡量;若是违背了“德”,便会产生“业”。其中,普通人的“业”是家破人亡,不得好死;而皇帝的“业”便是无可抗拒的天灾人祸了,洪捞,干旱,蝗灾,兵役。于此一来,皇帝作为“天之子”的权威才得以确定。若是如此分析,此人便是无可质疑的“业魔”了。人们敬畏且向往的,并非所谓儒家所论令人折服的“德”,而是令人痛苦且恐惧的“业”。
作为佛教文化同样昌盛且与中国一衣带水的东洋列岛,“业”却有着形势不同却内核相近的解释。如果从最常说的便是从“業火”这一词展开。业火被认为是“能烧尽烦恼,忧愁与欲望却不伤及身体的火”,而“业”便是业火的燃料。往往只有通过精深的佛理/哲学烧尽了“业”的人,才能得到大清净与大欢喜。不难看出,这里的“业”所对应的,便是精神世界上的痛苦与灾祸。“业魔”往往便是精神世界无法被满足而最终连理智也被所谓“业”一同吞噬的人。纵观其历史和文化。此类人比比皆是。从军国主义的嗜血天皇,《金阁寺》中的因孤独而焚寺之人,再到今天大把尝试割腕自杀的少年少女。人们厌恶所谓“业”,妄图得到清净,实际上却又无可避免的沉浸且依赖于“业”。
放到今天来讲,我认为前者便是欲望所产生的结果,而后者却象征着欲望所产生的原因。前者试图用道德来规范且约束欲望,从而改善可能的结果;后者妄图用佛学/哲学来消融欲望的产生,从让令结果根本性的消失,以避免可能的风险。
然而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了,所有对欲望的束缚最终都会成为形势主义的一部分,进而满足欲望。而所有对欲望的消解和压抑往往使得更为强烈的欲望隐蔽的产生,从而造成不可逆的后果。
而近现代西方文化对东亚文明的渗透则在这传统的因-果,消解欲望-约束欲望的二元坐标系,带来了新的单位向量。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达达主义,超现实和后现代主义,代表“释放欲望”的第三元就这样出现在了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从二十世纪初到现在,两者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强烈的对立,冲突与融合。
欲望与资本市场互相满足又互相催化,此刻无论是不洁的“因”,或是糟糕的“果”,都只能被生产力和其所代表的物质消解甚至正当化。我不知道,也不知道如何想象我的故国的社会与又会如何改变呢?这并非简单的(保守)-(进步)的对立,而是对人性,人权乃至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再次定义。
这一切如此剧烈且真实发生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很有幸却又痛苦的见证着这一切。